网络开赌场
网络开赌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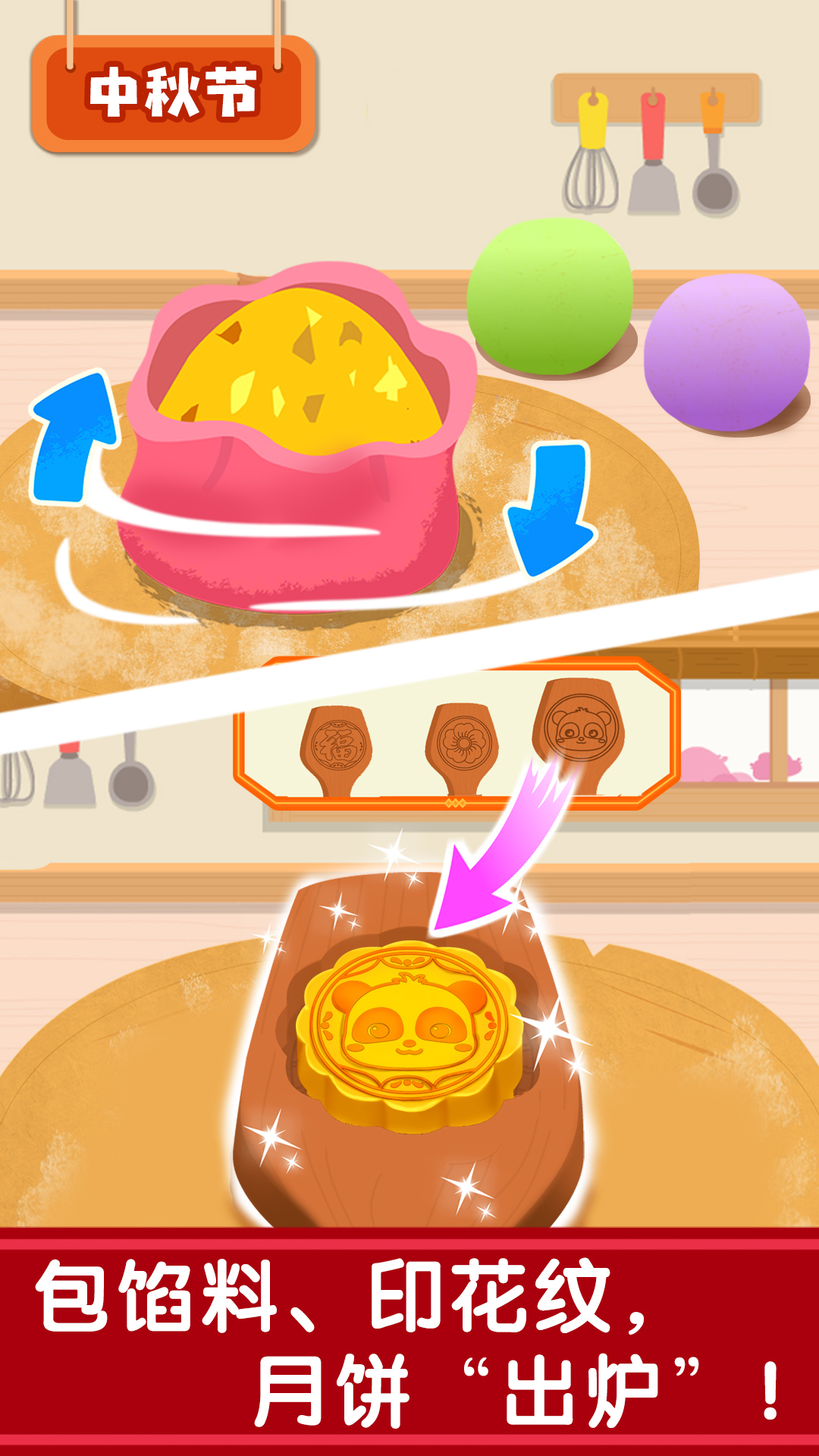

“至于妈妈,是我永远写不完的巨著,无法结尾的诗,她是不断使我追寻的逝去的时光,也是我日复一日的梦想,是寒宵中迷离的火焰。我早早地从她的手边荡开,很决然,但却始终不曾丢失她恒定的坐标,以便时时回到她的身旁。”陆源说。
4月14日下午,“只有离开故乡,我们才真正回到童年——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新书对谈”在北京竞园艺术中心刺鱼书店举行。作家陆源和宋阿曼一起,围绕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一书,聊起关于童年、故乡和写作的话题。对谈由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的责编广奈主持。

活动现场 (左起)广奈、陆源、宋阿曼
关于不同的“自我”
在对谈开始,主持人广奈谈道,人在成年之后对自己的童年大抵有一个审判的过程,譬如鲁迅写过《故乡》,高尔基写过《童年》。陆源的小说《童年兽》和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都是审视童年的作品,但两部作品中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。广奈提问道:“他们是同一个‘我’吗?还是说你觉得他们是不同的‘我’、一个人的两面,集合成一个完整的你?”
陆源坦言,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是按照非虚构来写的,当然也用了一些小说笔法和技术,但总体来说更真实一些。而《童年兽》从一开始就明确它是小说。小说写开了,写到某种境地,便顾不到所写内容与现实有多大偏差。小说遵循叙事逻辑,这一定程度上推动它往偏离真实的方向发展。
陆源说:“在《童年兽》里,有一个真实的我,这本小说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也有一个真实的我。所不同在于,在《童年兽》里,我为了文字的效果,呈现狂热中的悲伤、热烈中的黑暗,以达成某种矛盾统一的艺术效果时,我有意识地让自己成为一个受限之人。”
“受限”的意思在于,陆源写作《童年兽》时是三十七八岁,但假装自己处于一个更年轻的阶段,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,回忆自己十岁的事情。二十五六岁时的心境,显然“更激烈,更忧伤”。
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书写的正是当下,它呈现一个纪录片式的、没有滤镜效果的“当下之我”。“我以当下所思所想去回忆少年、童年的故事,不再像《童年兽》那样需要虚构一个,或者我要借用一个更偏执的我,以偏执的语调去回望童年。这是两者的差异。”陆源说。

关于“孤寒”
在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里,主人公是一个“孤寒少年”。“孤寒”这个词,原来出自陆源妈妈之口,对孩子的某些做法不认可,她便使用这个词。
陆源说:“这个词的含义,跟字面意思稍有出入。‘孤’是指孤单、孤绝,‘寒’是指卑微。但妈妈评价我‘孤寒’的时候,含义比字面意思更丰富。你不交朋友,没朋友,没人帮你,你也不想跟人社交,去沟通,去合作,那是因为你骄傲,而不是因为你孤绝而卑微,没办法结交一些权贵朋友,认识一些有实力的人。总之,卑微的意味没有骄傲的意味那么重。骄傲是因,而孤绝是果。”
宋阿曼由陆源的“孤寒”想到了另一层面。她说:“我以前觉得作家中很难有带着‘精英感’的人,可陆源就是。起初认识他,他就带着一种‘精英感’,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学金融。他身上有种劲儿,可以说是聪明或是睿智。直到我读到这本书,他写到家族里大多是顶聪明的人,用他的话说就是‘疯狂基因’,这说法虽然很好笑,但我突然释然了,‘精英感’,原来如此。”
关于“不幸对写作的馈赠”
在对谈中,广奈提到:“有人说不幸的童年是给予作家的馈赠,对于我个人来讲,我比较认同这样一个观点,就是你需要经历足够多以酿造美好的黄昏,当你书写的时候,这样一种不幸会成为你写作的馈赠。”
陆源认为,童年的不幸,倘若是真正的不幸,那么它将一直是不幸。它就像白纸上有一个墨斑,就在那儿,你可能远离它,从时间上空间上远离它,但它依然在那儿。作家利用这些童年资源,包括他童年的不幸,去完成一部作品,这在作家的认知之中当然是一种幸福,一种成就。完成一件艺术品,无论如何不是坏事。
“童年,你可以笼统认为,它是你的天时,是你的命运,有些东西决定于你出生前,你不可能改变。甚至,可以把它笼统归入天赋的行列。如果没有天赋,作家怎么去写作?时代也可以认为是天赋之一种。成为作家得有各种必要条件。但是,它从根本上不可追求,无关乎我们的后天努力。童年的不幸,作家不想要,或者想要,都没有意义。”陆源说。
宋阿曼则坦言:“童年的经历对创作者而言肯定是馈赠,不一定只有不幸的童年。我认为童年的快乐和天真的部分更重要,会更有慰藉性,也更能丰盈后来的写作。”
但她拒绝将不幸或苦难视作馈赠。她说:“幸或不幸,我们无法预料,或许客观上的确是某种生动的素材,但苦难本身不应该被歌颂。”
关于故乡或第二故乡
大部分当代人都有离开故乡和不断返回故乡的体验。谈及故乡这个熟悉的话题,陆源说:“当年身处故乡时,我认为很多事情好像从开天辟地以来应该如此。离开了故乡,去到了远方,甚至去到了外国,再回头过来看故乡,才意识到种种故乡的特性。‘特性’,之所以用这一个中性词,是因为它既然是优点,也是缺点。”
宋阿曼的中篇小说《啊朋友再见》开篇也讲到一个返还故乡的女性,时隔多年回到故乡,成了一个乡音浓重的异乡人。她说:“作家写故乡,其实是在写自己曾经熟悉的那个地方,是时间轴上的一个线段,那个固定时空的故乡才是故乡,才会给人安全的依靠感。作家一旦远离,定居他乡,似乎对故乡当下的面貌很少去描摹。可能曾经熟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变化,人才会对回忆中的那个‘曾经拥有’的地方产生依恋,才会仔细地去回味和描述。”
陆源坦言,事实上,自己在北京待的时间已经超过在南宁生活的时间,他从1999年来京读书,在南宁生活18年,在北京生活将近25年。“我觉得北京就是冷峻的爱。你承受了它的硬度,你承受了它的凛冽,然后你才可能喘口气,才有余力感受其中温情的东西。”
“有些朋友,长时间没有见面,其实生活在同一个城市。北京实在是太大了。但北京因着这些朋友,才形成一个北京的文化地图。所以北京不完全是地理上意义上的北京,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北京,甚至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北京。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,都不能提供我在北京这种稳固感。”陆源说。
采写:南都记者 黄茜